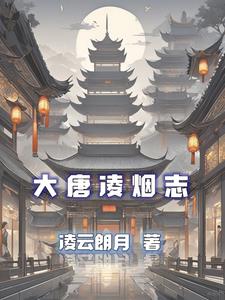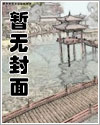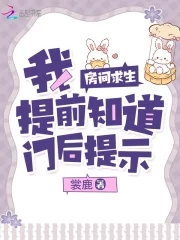公元620年底至621年初,正是唐朝统一战争的关键转折期。在长安周边广阔的战场上,除瓜州(今甘肃安西)刺史贺拔行威举兵自立、江淮李子通击败沈法兴自称吴帝、岭南冯盎稳定百越之地归附唐朝外,多个割据势力的剧变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发生,深刻重塑了天下格局。
在西北,武德二年(619年)五月,原本割据凉州(今甘肃武威)的李轨政权因内部分裂迅速崩溃,其尚书安兴贵作为唐朝密使,策动家族势力于里应外合擒获李轨,但凉州残余势力直至620年末仍在肃清,此役使唐朝一举控制河西走廊,打通西域通道。
中原腹地,洛阳王世充的郑政权虽被李世民大军围困,却因窦建德率十万夏军西援而暂得喘息,三方于虎牢关形成死亡角力;而河北的窦建德在驰援王世充前夕,其北部防线已现裂痕,恒山郡守胡大恩于武德三年(620年)十二月底举窦建德行台尚书令之衔降唐,此举虽未立即瓦解夏政权,却牵制了窦建德北翼兵力,为次年虎牢关决战埋下伏笔。
胡大恩是隋末唐初恒山地区(今河北正定一带)的重要人物。在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背景下,他投身于河北最具实力的起义领袖窦建德麾下,凭借才能获得重用。窦建德在河北建立夏政权后,任命胡大恩为行台尚书令,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职位,相当于夏政权在恒山及其周边区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,总管地方事务,这充分说明了窦建德对他的信任和其本人在夏政权中的地位。
然而,形势在唐高祖武德三年(620年)底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此时,窦建德虽然仍在与唐朝争夺天下,但秦王李世民已在中原战场上接连取得重大胜利,特别是击败了王世充,对河北形成了巨大压力。胡大恩所在的恒山郡,作为夏政权在太行山西麓的前沿地带,首当其冲感受到唐朝的军事威胁和政治攻势。正是在此关键时刻,审时度势的胡大恩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,主动向唐朝请降。
腊月的恒山郡,朔风卷着雪粒子抽打窗棂,城中行台尚书府内的炭盆噼啪作响,却驱不散笼罩在胡大恩眉宇间的凝重。案几上摊开的军报字字如刀:秦王李世民已扫平河东,兵锋直指河北;洛阳城下,王世充困兽犹斗,而主公窦建德正倾尽夏军主力筹备西援,整个河北北部防务如同被抽去梁柱的空架子,只留下他手中这万余兵马直面唐军的虎视与突厥铁骑的觊觎。粮仓将罄的消息更如最后一根稻草,压得他心头沉甸甸的。
当夜,府邸密室烛火通明,胡大恩召来了最信任的副将苏烈和掌书记崔文。他推开紧闭的窗,让刺骨的寒气与屋内的压抑碰撞,手指重重敲在案上那份标注着唐军动向的舆图,声音低沉却字字清晰,说道:“诸位请看。秦王已扼太行咽喉,我恒山悬于河北之北,恰似孤舟困于怒涛。夏王举国之力驰援洛阳,此去凶吉难料,即便功成,我北疆门户洞开,突厥狼骑旦夕可至;倘若……” 他顿了一顿,目光扫过两位心腹紧绷的脸,继续道:“倘若夏王有失,我等便是首当其冲的弃子。更遑论军中存粮,仅够半月之耗。”
副将苏烈,一位跟随胡大恩征战多年的虬髯汉子,猛地捶了下大腿,粗声道:“将军!咱们是夏王的臣子,血战到底便是!唐军虽强,未必啃得下咱恒山这块硬骨头!” 他眼中喷着火,却掩不住一丝对未知前路的焦虑。
“血战?为谁而战?” 掌书记崔文抚着稀疏的胡须说道,声音冷静得近乎冷酷。这位素以智谋见长的文士直视胡大恩,“将军,恕卑职直言。夏王此去,胜则洛阳归他,我恒山仍是边鄙;败则玉石俱焚。李唐已据天下大半,其势如日中天。秦王李世民雄才大略,用人唯才。且观其待杜伏威等降将,皆以王侯之礼,绝非虚言。” 他拿起炭笔,在“长安”二字上重重一圈,“此乃大势所趋。困守孤城,粮尽援绝,外有强敌环伺,内无生民之望,徒令恒山父老与我等同殉,岂是智者所为?将军明鉴,归顺李唐,非为背主求生,实为保全一郡生灵,亦为我等及麾下将士寻一条活路,觅一方前程!”
崔文的话语像冰冷的锥子,刺破了苏烈一腔热血下的迷茫。苏烈张了张嘴,想反驳,最终却只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,颓然坐下,盯着跳跃的烛火出神。
胡大恩的目光在舆图上唐军控制的区域与标注着“突厥”的广袤草原间反复逡巡。他沉默良久,密室内只闻炭火爆裂声与窗外呼啸的风雪。终于,他转过身,眼中那份沉重的犹豫已被一种下定决心的清明所取代。他走到苏烈面前,按住这位老兄弟的肩膀,声音不高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,说道:“苏烈,我知你忠勇。然忠义,非止于一人一姓。夏王待我恩重,我胡大恩铭记于心。但今日之势,守,是坐以待毙,赌上全城性命;降,或可存续薪火,保境安民。李渊乃李唐开国之主,气度恢弘。我等携恒山归附,助其安定北疆,共御突厥,亦是男儿建功立业之途!这非怯懦,是担当!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