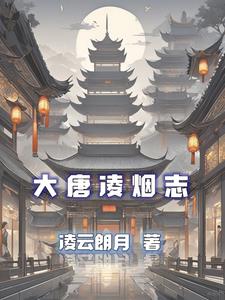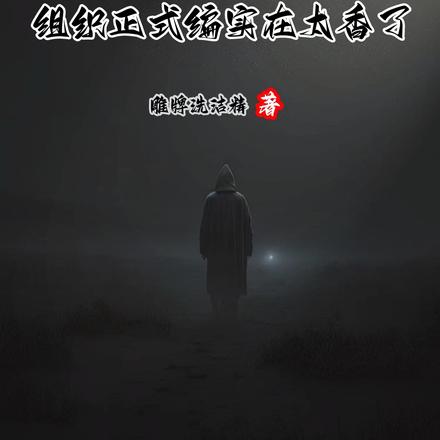武德三年(620年)四月,刘武周麾下大将宋金刚在介休之战惨败于李世民后,率残部北逃突厥途中,因与突厥处罗可汗产生矛盾竟遭腰斩。
此时刘武周正困守突厥境内,这位曾叱咤北疆的枭雄已陷入进退维谷之境。回溯其生平,刘武周本是河间景城人,生于隋开皇年间(约公元560年代末),少时骁勇善骑射,大业十三年(617年)趁隋末乱局,在马邑鹰扬府校尉任上联合突厥袭杀太守王仁恭,开仓赈济得军民拥戴,遂割据雁门、楼烦、定襄等郡,自封"定杨可汗",建元"天兴"。
其势力鼎盛时期(619-620年)联合突厥南侵,连克太原、晋州等地,震动李唐政权,然其过度依赖突厥的军事策略终成致命隐患。
当宋金刚主力在雀鼠谷与唐军八战皆溃,刘武周自知大势已去,遂于武德三年四月弃太原北遁突厥。此时正值处罗可汗统治时期(619-620年),史载处罗可汗"恃其强盛,有骄中国之色"。刘武周投奔后,处罗可汗虽表面仍任其为"定杨天子",实则视作傀儡。
刘武周此刻才回想起让其后悔的事情,当年(619年)秋,他在突厥处罗可汗支持下大举南侵,其麾下内史令苑君璋于大军开拔前极力劝谏道:"唐主李渊仅凭一州之众,就能直取长安,所到之处无人能敌,这实在是天命所归,并非单凭人力所能做到。晋阳以南地区道路险峻狭窄,我们孤军深入后路无援,若是进攻失利,到时候连退路都没有!不如采取北联突厥、南结唐朝的策略,自己则在南方称王,这才是长远之计。"
此谏言揭示三个战略要害:其一,李渊集团自晋阳起兵后摧枯拉朽之势实具天命;其二,地理环境对孤军深入的限制;其三,后勤保障的致命隐患。苑君璋进而提出"北连突厥,南结唐朝,南面称孤"的务实策略,本质上是要在突厥与唐朝之间保持战略平衡。
然而,刘武周当年综合势力正处巅峰时期,其"引兵围并州,齐王元吉委城遁",连克太原等要地使其产生轻敌之心,遂拒忠言,并自称"定杨天子"称号显露出代隋自立的野心,仅留苑君璋"领劲卒守朔州"。
至武德三年四月,李世民在柏壁之战中采用"坚壁挫锐"战术,截断宋金刚粮道,迫使刘军粮尽北退。当溃军退至朔州时,刘武周流着泪对苑君璋说:"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良言,才落得这般境地。"
此涕泣不仅是对战略失误的悔悟,更是对依附突厥政策的反思,其政权自大业十三年(617年)杀王仁恭起兵,至武德三年败亡仅存续两年余,暴露出过度依赖突厥骑兵的致命缺陷。败逃突厥后,刘武周虽被处罗可汗封为"定杨天子",然其"寄居虏帐,号令不出营门"的傀儡处境。
巧合的是,处罗可汗当年(620年)冬突然暴卒,颉利可汗继位,对刘武周猜忌更甚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载,刘武周在突厥"郁郁不得志",其苦心经营的割据政权自起兵至覆灭仅维持三年余(617-620年)。这位时年约五十余岁的军阀不甘寄人篱下,暗中联络旧部欲重返马邑,最终因其密谋泄露,颉利可汗为绝后患,将其诛杀。之后,其部将苑君璋虽受突厥册封为大行台继续统辖余部,但刘武周集团实际已名存实亡。
刘武周势力的兴亡轨迹印证了《旧唐书》"始则假突厥为声援,终乃为突厥所戮"的历史评判。
《旧唐书·刘武周传》评其"武周始为鼠窃,偶恣鸱张,不用君璋之谋,竟为突厥所杀",《新唐书·刘武周传》史臣赞的写道:"武周藉突厥资,盗据边陲,然无远略,故兵随之亡。"揭示其借势而起、失势而亡的必然命运。
然而,从历史维度观之,刘武周集团的存在客观上牵制了李唐北进,为李世民经略河东、锤炼军事才能提供了特殊战场,其兴亡轨迹亦折射出隋末群雄依赖外族终难持久的时代特征。
刘武周割据政权在唐军雷霆攻势下土崩瓦解,这场历史性转折犹如重锤击破冰封湖面,于隋末唐初军政版图中引发连锁震荡,深刻重塑了整个时代的权力格局。
占据河北的割据势力窦建德听闻刘武周覆灭的消息后,一股寒意袭上心头,被迫做出唇亡齿寒的战略调整。他坐在营帐之中,眉头紧锁,不停地来回踱步。
谋士凌敬在一旁劝道:“大王,刘武周与咱们虽非盟友,但同为割据势力,如今他败亡,大唐下一个目标恐怕就会是咱们了。”
窦建德听后,停下脚步,重重地叹了口气:“唉,这李渊父子确实厉害,刘武周那样的劲敌都被他们打败了。如今我河北之地,虽兵强马壮,但也得早做打算啊。”
于是,窦建德下令加强防御工事,在边境地区增派重兵把守。同时,他派遣使者前往洛阳的王世充处,商讨联合抗唐之策。
窦建德在信件中诚恳地写道:“王兄,如今刘武周已灭,大唐势力渐强,我等若再各自为战,恐难自保。不如联合起来,共抗唐军。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